今天,我回到了這裏,這個伴着我度過了大半輩子的地方,而我卻好像已經不認識這裏了,面前的海灣已經消失,變成了一堆高樓大廈。昔日的寮屋區已經變成了兩個屋邨。我認得的只有這個叫靈實醫院的地方跟這個依然在的山頭,不知道我走上去,那個碉堡是否依然在呢?
如今再臨這裏,種種往事擁上心頭。當年,我丈夫是少數依舊追隨國民政府的士兵,國民政府戰敗後,丈夫回到廣州找到我,打算趕上退守臺灣的船,只是趕不上,我們只能跟着同樣無法逃到臺灣的同伴匆忙地逃到香港。港英政府把我們安置到摩星嶺難民區,直到1950年6月18日,那日正好端午節,有八十多名學生來到我們這裏跳秧歌舞,共產黨常用這種慶祝方式來挑釁我們,丈夫被他們惹得有些生氣,不過最後在我規勸下忍了下來。有些急躁的同伴便跟他們打了起來,演變成流血衝突。當時我十分慶幸丈夫沒有跟着起哄受傷。政府便把我們全遷到調景嶺。
剛剛抵埗的時候,這裏就是一片寸草不生,荒蕪的山頭,我們被安排住在油紙棚屋內。我們起初認為國民政府很快會反攻內地,很快我們就能返回家園,跟在內地的親友團聚,或者被接到臺灣重新開始。根本就沒有想過我們這一安頓便是一輩子的事了。兩年後,臺灣派來中國大陸絲盹救濟總會,同時教會也一直提供援助給我們,大家得到支持,開始興建寮屋、出外找工作,調景嶺慢慢便發展成了小社區,大家都慢慢地過着安定生活,慢慢地落地生根,彷彿遺忘了反攻內地,或者搬回臺灣的夢兒。
那時候,我也在寮屋裏做點手工針線活幫補着,生活也漸漸好過起來。我們這兒的治安很好,居民守望相助,警察跟我們的關係很融洽。丈夫不用外出工作的日子,我們便到白石柱看着海景,悠閒一番。或者是坐在那周邊掛滿國民政府旗的渡口,看着一望無際的大海。我知道,其實丈夫一直都很希望國民政府能夠反攻內地,其實我明白,雖然在這裏的生活很安穩,我們也育有了一群可愛的孩子,最終他們也能到臺灣繼續學業,大展所長。為人父母的最大的心願不過於望子成龍,望女成鳳。但是這種寄人籬下的感覺還是如此的強烈!不過,這麼多年,我也知道這是不可能的事了。我也早當了這兒是我們的家,這麼多年,總是有感情的。
如今再回來,看到一片截然不同的景象,其實我也不意外,早就聽說了,1984年中英聯合聲名敲定的時候,已說了1997年,這香港就會回歸中國,就是共產黨。如此,它又怎會容許如此有國民黨氣息存在的地方繼續留存?果不其然,寮屋區被清拆得無一絲痕跡可尋,彷彿根本從來都不曾存在般。曾經在這裏處處可見的國民黨青天白日旗現在是無影無蹤了。我真是慶幸我不用看見這寮屋區夷為平地的那一剎,或是海灣被填為土地的那一瞬間,就讓這一切停留在我心裏最美的時刻。其實我真的很痛心:對舊家園的不捨,為海灣而惋惜。現在,我想做的便是到碉堡那裏,那個我唯一有熟悉感的地方,碉堡,把回憶找回來。我認為人的一生,最寶貴的就是回憶。其餘的,都不重要。其實來到這裏,佔據得最多的心情不是悲傷,是回憶,滿滿的回憶,非常的滿足,感謝上帝給了我一個跟別人不同的一生,給了我不同的經歷,不同的體會。
評論與回應
本站聲明
1.本網站保留刊登或刪節留言的權利,並有權在不作通知的情況下刪除討論區上的任何內容。
2.公眾用戶在本網站的留言均為留言者之個人意見,不代表本網站的立場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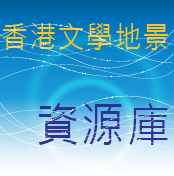
再加長一點,就是一篇小小說了。投入人物的心境,重構當時環境,故事完整,國民黨故人如歷歷在目。末段碉堡處可加入更多描寫,承托物是人非的抒懷。
佳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