耳畔傳來了某種生物的悲鳴聲,當中還夾雜着微風吹拂浮雲的流動聲。
還在沉睡中的我,被這些細微的聲音給喚醒。我緩緩地睜開雙眼,視野還沒能清晰地對焦外界事物,只隱約看見一個淡青色的模糊輪廓,以及那令人刺眼的銳芒。這讓我下意識地抬起傷痕疊疊的手,遮住雙眼。
手背被夕陽的光芒所籠罩着,我微微一怔,心裏的深處淡淡地漾起一波漣漪。是的……我很久沒觸碰過這所謂的溫暖,這略頗滾燙的溫度讓我有點不適應,因為我在外流浪已經將近快十年了。
驀地,在我粗糙的指尖上停留了一隻蜻蜓,是那淡青色的綽影。它那輕柔的觸碰, 猶如就在那瞬息間,它連接了我的脈絡,那脈絡間的微絲血管裏,流淌着的是蜻蜓身上的青蔥色澤。它的翅膀如此纖薄,在黃昏的光芒下幾乎透明,只有一層似有若無的色澤。它輕盈地撥動翅膀,彷彿為我撥開眼前氤氳在空氣中的光塵。我隨着它移動的身影踉蹌地站了起來,眼前是一片芒草。
天空失去了原色,像飽飲了玫瑰酒似的,醉醺醺地漲溢出光與彩。不知從哪個方向的微風輕拂着礦野裏的一大片芒草,湧起層層的金色波濤。遠看,一株株芒草更彷彿是柔和的光焰,影影綽綽地搖曳着輕盈的身姿。
我半瞇着雙眼,正當享受這刻靜謐的瞬間時,被遠方的喧嚷聲所吸引。遠眺看去,看見一位老伯站在一個被歲月沖刷的礁石上,身上只穿着單薄的白色背心,手上搖着薄扇,旁邊圍着幾個活潑亂跳的小孩,拉着老伯的衣角,不知在嚷鬧着甚麼。我撥開芒草,將要跨上礁石,卻沒留意地上被人隨意擺放的鐵管,一不小心被絆倒了腳。身子失去重心向前一傾,手掌碰蹭到尖銳的礁石,一陣劇烈的痛楚直達我的神經。
我咬緊牙關,低頭看着兩雙手掌都冒出血泡,指間的罅隙還殘留着灰黃色的沙石。倏然,一把低沉渾厚的嗓音傳入我的耳畔。
「小子,上來吧!」老伯嘴裏叼着廉價的香煙,伸出黝黑的手掌,抓住我的手腕,一下子就讓我輕鬆地上到了礁石。
我連忙上前與他說了聲道謝,但臉上還是有點窘迫,畢竟在一群小孩子面前糗了洋相,心裏可不是滋味。但我還感覺到手腕那有力的遊度和他雙手佈滿老繭的觸感,給我一種飽經風霜的感覺。
「老伯伯,老伯伯!快點給我們講講當年你做礦場工人的經歷吧!」一個小女孩奶聲奶氣地纏着老伯的手臂,滿眼閃爍着好奇的微光。
「對呀!對呀!快給我們講講吧!」其餘的小孩都急迫地應聲道。
我聽到這段話時,心不禁咯噔一下,對着面對自己抽煙的老伯,聲音帶有顫抖:「您……您可知道當年鄭氏後代鄭連昌在族譜中所說的隱言?」
老伯微微側過身,乾澀的唇瓣間悠悠吐落出成絲成縷的灰色煙霧,在惆悵的夕陽下,遲重的濃灰漸漸地往他臉龐上升騰,又漸漸地消隱。老伯搖了搖手中的薄扇,淡淡地笑言道:「我只是一個普通的礦場工人。」
我聽完之後,有些黯然地垂着眸子,左手從破爛的褲袋裏拿出一張泛黃的地圖。地圖上顯示了鯉魚門的所有地理位置,曾去過的地方都會用油性筆記錄下來,如今差不多走過鯉魚門的每一個角落,但就是找不到那所謂的寶藏族譜。
老伯用余光向地圖瞄了幾眼,似非似笑地問道:「小子,特意前來尋找鄭氏的寶藏?」
我像小雞啄木般點點頭,用手背拭去地圖上的灰塵,有些感歎地道:「這個地圖是上幾輩流傳下來,我曾祖父曾經是一位探險家,他就拿着這張地圖找了整個鯉魚門一遍,結果到頭來也還是未能找到。」
說完,我和他都不再說話,保持緘默。只見那群小孩津津有味地聽着我們的對話,有一個男孩頑皮地捧着雙手,想去接過老伯手上香煙掉落的灰燼,那一團黑的灰燼裏還能隱約地看見灼熱的星火。老伯向男孩瞪了一眼,那男孩嚇得連忙怯怯地將雙手縮回了背後。
此時此刻,我偷偷地打量着老伯。他身型有些佝僂,臉上留下一道道被歲月刻磨的皺紋。那一雙棕褐色的眼睛深陷在眼窩裏。他有些凝重地望着一望無際的大海,不知正在深思甚麼, 眸子裏似乎有一絲光彩閃過,那光彩流轉着。
***
我折返到天后廟,心裏躊躇些甚麼,我說不上來。我掏了幾個零錢買了幾枝線香,然後雙腳屈膝地坐在拜墊上,雙手合十,向佛祖磕了幾個響頭。接着,我起了身,將三枝線香插在香爐裏,被燃點中的線香如屑般飄落着苦澀的灰燼,如同老伯嘴裏叼着的香煙。
我怔怔地望着從香爐裏飄出來的煙氤,如靈活的青蛇盤繞成一圈圈,愈盤愈高,閑散地在空中輕柔地晃動着。
我是虔誠地祈求自己能順利奪取鄭氏寶藏嗎?
突然,我回想起剛才老伯對我說的那番話,那意味深長的話。
「我從高祖父那一輩開始便是從事礦場工人,一生平凡。我曾聽父輩那一帶說起,當時明敗清起,明末遺民紛紛南逃,導致在高祖父那時期曾遇到過鄭氏後人,他們因為勢所逼,淪為海盜,並盤踞了鯉魚門一帶。由於鄭連昌為人凶悍,於鯉魚門後山設寨,更被當地居民稱為惡魔頭,因而山名亦稱為魔鬼山。
你所說的鄭氏族譜裏,曾流傳一句話,三叉水溝,鯉魚疊石八尺高,黃沙是金子,祖先大事可修。這句話如果你能領悟到意思,或許你真的能取得鄭氏寶藏。不過,你一生就只追求所謂的寶藏真的有意思嗎?我家裏本來就貧僚,對於寶藏這些看似虛妄的東西,我自然沒有興趣。我這幾十年來,一生就從事礦場工人,每天日灑雨淋只懂得搬礦石,我真的是普通再普通不過的礦場工人呀!」
天邊的晚霞傾灑下來,投下一大片橘紅的柔光。老伯靜靜地佇立側身面向大海,半邊身子被仙氳般的霞彩籠罩着。那話語中似乎帶着沉重的遺憾,追憶着他曾逝去的青春。
我走出了天后廟,不知從而何來的決心和堅定,催促我來到海灘。我登上了墨綠色的燈塔,雙手靠在欄杆,還意外地發現欄杆角落有一個缺口,在那長了一個萎靡的花草,我笑了笑,不知為何腦海又浮現老伯的臉龐。黃昏的微風吹掀起我額前的碎髮,讓我更清晰地看到海面上跳躍的碎光,海浪翻滾沖刷礁石的聲音,漸漸地淹沒在一種模糊的寂寥中。
重新掏出地圖。
我緊抿着唇,將手中握住的地圖輕輕一放,那張地圖就那麼不捨地從我手中離去,就那麼地對我說了聲「再見」。我就這樣看着地圖消融在玫瑰色的大海中。
但在同時間,我錯愕地眺望遠處的海面上,竟有鯨魚的影子。它們從海面上翻轉,深藍色的皮膚發着光,然後躍回大海。它們發着冗長的悲鳴聲,重新又躍起。鯨魚們在窅暗的深海盤游,游動如呼吸的行星。
海面依舊是閃爍躍動。
它們是為我一生在盲目地尋找寶藏而感到悲哀嗎?
在逐漸變暗的天空下,我闔上雙眼,開始沉思。
評論與回應
本站聲明
1.本網站保留刊登或刪節留言的權利,並有權在不作通知的情況下刪除討論區上的任何內容。
2.公眾用戶在本網站的留言均為留言者之個人意見,不代表本網站的立場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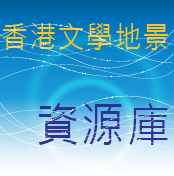

情節完整,敘述也有條理,而且運用鯉魚門的景觀去開展劇情,而不覺得突兀,顯然花了不少心思,值得一讚。另外你運用了不少意象,去突出了主角的情緒,情景配合得宜,不流於抽象,勝過同一輩的作者。題目的虛妄也貼題!